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树下》:连接过去未来当下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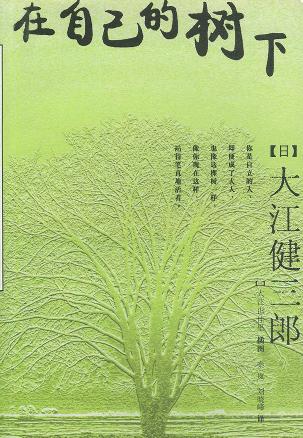 |
| 大江健三郎 《在自己的树下》 |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大江在这个时期的部分创作活动:
2000年12月,由讲谈社出版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
2001年6月,由朝日新闻社出版随笔集《在自己的树下》(大江由佳里 配图);
2002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长篇小说《愁容童子》;
2003年9月,由朝日新闻社出版随笔集《致新人》(大江由佳里 配图)
2003年11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长篇小说《二百年的孩子》;
以上作品中计有随笔集两部,长篇小说三部。
就体例而言,随笔集皆配以夫人大江由佳里的水彩图画,色彩鲜艳的封面画作和文中插图与相关内文可谓相得益彰,以至一些读者来信要求夫人“画得好才令人喜欢,就这样画下去”。在文体上,尽管作家在第一次专以孩子们为对象写下的《在自己的树下》中,“因为想写的东西太多,结果把为小学高年级的孩子们写的东西和为已经读了高中正准备考大学的人写的东西都写了进来”,该随笔集和其后的《致新人》)由于使用了此前罕见的简洁流畅的平实口语体,仍然受到从小学高年级学生到高中生的广泛欢迎。即便对于专事研究大江及其文学的学者来说,这些随笔中蕴涵的信息也是非常宝贵的。
至于那三部长篇小说,就文体来说,也与大江以往的小说语言风格大相径庭,少有初期作品中因存在主义影响而导致的语言方面的标新立异,也不见接受俄罗斯形式主义影响后所追求的语言陌生化处理。尤其是《二百年的孩子》,更是用顺畅平实的口语文体书写而成,至少就语言意义而言,大大降低了文本的解读难度,使得文本的阅读年龄层甚至可以下行至12岁左右。当然,联想到作家此前在随笔集《宽松的纽带》中所说的“如果以后再写小说,也想创造一种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新文体,因为我的发愿、发心原本就是希望创作形式上标新立异的小说”,当下的这些变化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标新立异和陌生化处理?!
我们还可以从这五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发现另一个显著变化——这位作家不仅在书名里醒目地含有孩子、童子和新人字样,其内容亦以孩子、童子和新人为主题,即便在文本之外,也不断出席以孩子、童子和新人为题的各种演讲或读书会等活动。就读者对象而言,这些作品中有些原本就是为孩子们而书写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作品中包括体例、文体和主题等方面的变化,不可能只是作者的一时心血来潮,而只能是其深思熟虑的慎重选择。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几个问题——作者从事创作四十余年后,为什么在近期出现这个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下和未来又具有哪些意义?我们将在解读以下作品的同时尝试求出解答。
《被偷换的孩子》原著题名旁加注的片假名表明,这个书名缘自于英语词汇changeling,说的是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而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了。吾良显然就是这样一个changeling,从这个名字的字面上看,他应该是一个“我本善良”的人物,却被一伙国家主义分子以其青春而健康的肉体为诱饵,将美军军官诱至山中杀害并夺走佩枪……这帮国家主义分子在毁灭美军军官皮特生命的同时,也将英俊少年吾良的善良和纯真也一同毁掉了。当然,最终彻底夺走其生命的是另一些戈布林——疯狂报复的黑社会暴力团伙和大肆炒作所谓绯闻的不道德杂志等媒体。
也是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长江古义人(也是贯穿其姐妹篇《愁容童子》和《再见吧,我的书啊!》的中心人物)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战败那年秋天,他拿着植物图鉴进入森林,却因突发暴雨困于林中,直到三天后被上山救援的人从树洞中解救出来。弥留之际,他依稀听到大夫嘱咐母亲准备后事。醒转过来的古义人便询问母亲自己是否就要死去?母亲却告诉古义人他不会死去,即便真的死去,她也会再生出一个孩子来,“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所知道的词汇说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
森林里的这个故事源自《在自己的树下》中大江儿时的一段真实经历,就方法论而言,这个故事为吾良的再生提供了可能,也为许许多多被戈布林们偷换走了的美丽而纯洁的婴儿提供了再生的可能。恰巧吾良的昔日女友此时已怀有身孕,堕胎前无意间阅读了这个关于孩子再生的故事,便决定“要为死去的孩子再生一个孩子。把死去的孩子的所见所闻,所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他听……我要成为把死去的孩子讲过的话教给新孩子的母亲”。……在作品的结尾处,大江借用千樫之口引用了索因卡的一句台词——“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无疑,这里所说的“尚未出生的孩子”象征着美好的未来。在主人公古义人(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大江本人在文本内的分身)的眼中,一些疯狂追逐经济利益的戈布林毒害了我们的社会,践踏了人文精神,即便少年一般纯洁的吾良也难免不受其污染,最终不得不被迫走向毁灭。与此同时,另一些戈布林则鼓吹新帝国主义理论和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严重恶化了国际环境,使得世界和平以及人类文明的进程受到极大威胁。对此表现出强烈忧虑的大江在作品中期盼并呼吁一代新人的出现,呼吁那种没有遭受污染、象征着人类的良知、纯洁和美好未来的新人的出现,呼吁人们与索因卡一同喊出“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
《被偷换的孩子》的续篇《愁容童子》的舞台还是在四国那片森林里,早已成为著名作家的长江古义人带着长子阿亮和美国知识女性罗兹回到故乡,“希望具有方向性地探究步入老境后的人们所面临的生与死的问题”,并重新审视在故乡广为流传却少有官方记载的“童子”故事,却遭受到来自各方——死而不僵的国家主义余孽、根深蒂固的神社、甚嚣尘上的财阀、与古义人同时代的转向知识人、象征强势文化和话语暴力的当地报纸——的敌意。但文本内的古义人一如那位愁容骑士般不知妥协也不愿妥协,因而也就只能照例接二连三地受到肉体和精神上不同程度的伤害,最终在深度昏迷的病床上为这个如此伤害了他的世界进行祈祷——“曾彼此杀戮的人们,相互被杀的人们,宽恕吧!必须准备随时互相厮杀的幸存者们,宽恕吧!……”
文本中对古义人充满敌意且给他的肉体和精神造成巨大伤害的“故乡”,正是文本作者大江健三郎多年来在小说世界中苦心建构的那个“共同体/根据地/乌托邦”!遗憾的是,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共同体/根据地/乌托邦”即便还没有分崩离析,至少也是摇摇欲坠了。大江在以往作品中赖以建构根据地的最为重要、也最能体现边缘性特质的材料——森林中代代相传的传统和记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势者改写甚至抹杀,遭到被中心文化严重侵蚀的家乡少年的抵制。也就是说,家乡的边缘性特征已被严重弱化,在被来自外部的中心文化日益同化的同时,在家乡内部还受到神社、国家主义余孽、当地媒体、向右转的知识分子、鄙俗的暴发户等新旧保守势力的改写、抵制甚至抹杀。尤其在当下的日本,在国家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的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逐渐沉入“黑暗时代”的“故乡”原本具有的真正意义上的边缘性特征正在被解构,当然,大江多年来苦心建构的“共同体/根据地/乌托邦”也不能不面临被颠覆的严重威胁。面对这个严峻局面,大江首先抓住了“在那危险的时刻闪现在心头的某种记忆”——祖辈代代相传,却被强势者改写抑或抹杀的神话/传说,并对这些故事进行叙述或重述,以唤醒在更多人内心底里沉睡不醒的相关传统和记忆,从而重构“故乡”的边缘性特征,在黑暗中发出些微的光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江在文本内提及的强势者和弱势者的相对关系,不仅存在于某一特定群体、民族或国家内部,同样也存在于集团与集团、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这就赋予该文本以更为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另一个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是在大江抓住并叙述或重述的记忆中,童子占据了无可替代的核心位置。不仅在这部作品里,即便在其后创作的《二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中无不如此。
当然,作者本人也清楚地知道,对记忆中的神话/传说进行叙述或重述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在当下这个“人心在晦暗中徘徊”的“黑暗时代”。于是,大江这位早已成为少数派的民主主义作家开始考虑一个令人无比震撼的选择——必要时去往彼界,化为诸多童子中的一员,在无际的时间和空间里努力复原被强势者所改写、遮蔽甚或抹杀了的弱势者历史,以此与强势者所书写的不真实历史相抗衡。实际上,文本中的主人公古义人在弥留状态中正一步步地挨近那个世界。
在另一部完全以孩子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二百年的孩子》中,古义人则是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存在,小说主角是乘坐做梦人的时间装置往来于以往、当下和未来的兄妹三人。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这兄妹三人是以作者的三个孩子为模特的。在文本中,他们听说在父亲长江古义人的故乡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当地传说中的童子只要在森林中千年柯树的树洞里合眼入眠,就能够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看到自己想见的人和事物。兄妹三人为了见到去年已经去世的祖母,便在暑假期间来到林中找到那个树洞,并在《宽松的纽带》中曾提及的小狗“腊肉”引领下,邂逅了在120年前拯救村子于危难之中的神奇童子铭助。为了救治在逃跑中受伤的孩子们,他们回到现在的社会里取回喷雾型消炎药,为暴动的农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却无法改变业已凝为历史的以往事实。这三个孩子还邂逅了在103年前的明治初期到美国留学的第一位日本女留学生。当然,本书的作者没有忘记安排这三个孩子以同样方法前往2064年的世界各地,想让他们看看未来那个时代的高度管理型社会是否充满光明。倘若情况并非如此,孩子们将会从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开始努力学习,以积蓄改造甚或创造光明未来的力量。
如同前几部小说一样,这部小说的舞台仍然设定在位于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之地——四国森林之中,孩子们得以自由往返于1864年至2064年这二百年间所乘坐的时间装置,正是《愁容童子》中做梦人借以联络诸多童子的机械装置。显而易见,作者在用当下的孩子们所熟悉的平实语言,向他们叙述民间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具有代表性的童子故事。如果说这种叙述有了较大变化的话,那就是通过祖母、父亲和姑母开始与这片森林中的神话/传说产生内在联系的兄妹三人已然成为新一代童子,得以连接以往、当下和未来的新型童子。当然,他们还负有一种使命——改造甚或创造光明美好的未来。这大概就是作者对他笔下有关新人的界定吧!
自传性较强的随笔集《在自己的树下》是大江在“漫长的作家生涯中,第一次这样为孩子们写的一本书”。在收入的16篇随笔文章中,作者分别以逃学、生存、语言、反战、学习方法以及反对自杀等为不同主题,向小学高年级到中学的孩子们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和成长经历,当然,其中不乏我们在《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中为之惊奇的故事和事件的原型,比如“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中母亲对尚未脱离危险的大江所说的有关再生的故事;“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中祖母讲述的有关自己的树的故事;“孩子的百年”里母亲在树下讲述的童子传说中有关农民暴动的故事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儿时听到的这些故事,不仅使大江受到了文学的最初启蒙,还为其在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之地构建“共同体/根据地/乌托邦”提供了最为重要、也最能体现边缘性特质的材料——森林中代代相传的传统和记忆。
《致新人》同样是一部面向孩子们的随笔集。其实,早在这部随笔集问世前20年,大江就在短篇小说《新人呀,醒来吧!》里运用了新人这个源自于英国诗人布莱克预言诗中的隐喻,试图借助这个隐喻使那些处于危机之中的人获得再生。从那时开始,新人便成为大江在不同作品和不同场合频繁使用的一个关键词。
就通常意义而言,《致新人》收入的15篇随笔文章确实可以多角度地为孩子们提供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智慧,但这种功能肯定不是作者想要向我们传达的主旨。逐渐步入老境的作家在结束自己的作家生涯前,更希望日本的、亚洲的、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成为新人,能够连接以往、当下和未来的新人,能够尊重以往历史并开创美好未来的新人。因为这位作家知道,如果他们不能成为新人。这个世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未来!
在大江另外两部随笔集(《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中,作者用同样朴素的口语体叙述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间的温情。透过这些与他的小说语言截然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随着作者一同体验面对智障儿子光的苦恼,发现光的音乐天赋时的喜悦,进而从家庭内部和作家心灵深处观看外部世界,观看大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观看形成大江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大江健三郎 《在自己的树下》 |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