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切问近思:读《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
如所周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作为中华文化的根干,儒学在日本也有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影响并未随着“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进程而消逝,相反,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建立现代大学以后,主要的汉学家基本上都有一本与孔子或《论语》相关的著作。这个传统流传至今,迄未改变。作为当代日本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史家,子安宣邦先生历时六年,与市民一道重读《论语》,从而完成《思想史家が読む論語——「学び」の復権》(岩波書店2010年),其中译本《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于201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行。

切问近思:以古学之法重读《论语》
大概可以说,《论语》是先秦诸子中最容易读进去的一部典籍。掀开书页,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到鲜活生动的场景和栩栩如生的面容。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经典难读,所谓“过往即异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渺远的时空横亘于古今之间,更别提操着不同语言的他邦之人了。子安先生切切实实点出了阅读的困难:《论语》中的很多概念,我们已难以理解,因为今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和古人迥然有别,“就算我们能通过后来中国礼教世界的发展来理解‘礼’的重要性,孔子的教示中涉及的‘诗’与‘乐’的重要性,我们未必就能够很容易理解,因为‘诗’与‘乐’早已不再在现代世界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了”。
然而,古代经典不是有许多当时和后世的大儒为之作疏作注么,经由这些诠释,借助这些扶梯,我们就不能接近先贤的思想吗?的确,这是一个途径。不过,这条路仍然充满荆棘和陷阱。作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论语》的文本上已经累积太多前人的解读,而我们自己的阅读也只能通过这些解读来进行。想用全新的眼光来阅读完全不沾染任何前人理解之痕迹的全新古典文本,不啻天方夜谭”;另一方面,像朱子那样的旷世大儒对《论语》的解读被典范化之后,《论语》本身的内蕴却被遮蔽了,朱子的《集注》不期然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怎么办呢?专攻江户日本思想史的子安先生的途径是“曲线读孔”,江户时代古学派的两位大师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成为他的思想资源,仁斋著有《论语古义》,徂徕著有《论语征》,更重要的是,这两位儒家思想者都带有批判的意识——仁斋以批判的眼光重读朱子《集注》,徂徕则以批判的眼光阅读仁斋和朱子。具体言之,则是:
我们通过思想史的解读,将遮蔽了《论语》文本的众多解释作为后世附加的而将它们相对化,从而使《论语》文本的原初性在解释的彼岸显露。这并不意味着发现的是《论语》的原初文本,我们发现的,是敞开了更多可能性的文本,是我们能够通过叩问而获得更多意义的可能性的文本。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开始意识到,孔子自己其实是在不断地反复问‘什么是学’‘什么是道’‘什么是政’‘什么是礼’这些问题”。这使他恍然,在古代思想文化的很多问题上,孔子一直在叩问——这种“每事问”的精神才是孔学的精髓。从仁斋的“论语古义学”出发,作者在重读《论语》时,也尝试着在字里行间反复叩问孔子曾经问个不休的问题——
没有叩问的“学”只能是空疏之学。然而,这种叩问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于对切近己身的各种事情的思考。……经由这种“本质性的重问”,作者打破了前人种种解读所造成的壁垒,使《论语》成为一个“敞开了更多可能性的文本”,可以去探索《论语》所蕴涵的意义。其结果是,“我不止一次地体验到,在梳理诸家的解读之时,我听到了孔子之言发出的新鲜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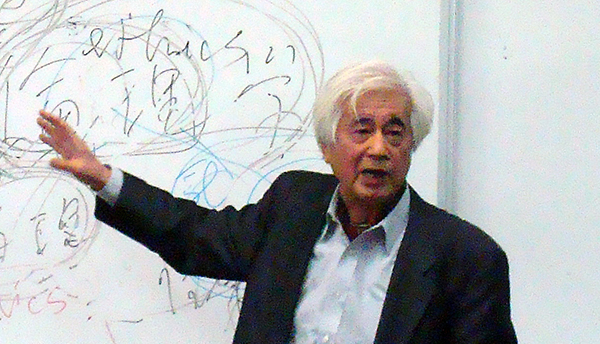
子安宣邦
回到孔子:注意分辨解释性的言说
明确了子安先生重读《论语》的方法后,我们再来看他实际是如何操作的。
从目录可知,本书前有中文版序、导读、绪言,后有跋文和索引,中间部分是主体,包括二十三讲,前十八讲讨论一个或两个概念,先列出《论语》中的相关语录,然后征引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涩泽荣一、朱熹等各家注释,阐析孔子的核心思想,后五讲是“弟子们的《论语》”,从孔门弟子的视角(曾子·子夏·子贡;樊迟·子游;子路;曾皙·冉有),重估孔门师徒的言行。而且,选择的篇章不避重复,其中“德”就占了两讲(第六讲论“德”,第十讲怀“德”),像“为政以德”一章,就同时出现在论“政”、论“德”两讲当中。也就是说,《孔子的学问》跟常见的《论语》诠解不同,它并没有采取全文照录、字义疏解、疑难串讲的方式,而是以关键词为中心,有类“孔门宗旨导读”。
为了追寻《论语》的古义,就很有必要辨别“解释性的言说”。像朱熹这样的后儒的解读,我们似乎比较容易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由于《论语集注》在解释学上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空气中,形成压抑的文化氛围,人们虽未开卷,却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厌恶和反抗。子安宣邦就表示,朱熹对“克己复礼为仁”这一章的解释,引申出孔子教导的规范性、教诫性的言语,造成的影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虽然一直在读仁斋的《论语古义》,却始终没有直接阅读《论语》的兴趣”。对于朱熹,我们有排拒心理,有一种“谨防上当”的自觉,而对于《论语》中的解释性的言说,我们往往会忽略不计。《学而篇》第二章是有子的话(君子务本),第四章是曾子的话(三省吾身),第七章是子夏的话(贤贤易色),我们通常是“一视同仁”,都当作孔门要旨,或者说是孔子精神的发挥,而作者特地说明:“后孔子的有子的发言本身,就已经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性的言说。”同样,对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作者也强调这是一种后孔子的解释性言说。对“信”字作了一番寻根追源后,作者敏锐地指出,虽然“‘信’字被训读成了‘诚’(实,まこと)”,但“诚”的概念是“在孔子之后,尤其是《中庸》之后的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讨论“死生·鬼神”时,书中也有清晰的分辨:“《论语》中孔子关于鬼神论的言说,可以说是一种原鬼神论。围绕着这一言论展开了三种不同的鬼神论。首先是朱子的鬼神论,接着是仁斋批判朱子的言论,最后是徂徕批判仁斋的言论。”在作者看来,朱子是解释性的鬼神论,仁斋是无鬼论,徂徕则是有鬼论,可见其分歧之大。
以“仁”为例,试看作者是如何进行“本质性的重问”的。朱子采取了下定义的方式:“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钱穆在解释有子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时,是顺着孟子“仁,人心也”来阐发的——注意,钱穆在此并没有把孔子、有子、孟子分别对待,而是视为孔门教学的三种形态,其主旨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认为,朱子进一步把“仁”说成“天理”,“如此一抽象,就失去了那活生生、活泼泼的人的具体感性情感内容而变成君临事物的外在律令,歪曲了‘仁’不脱离情感(本体不离现象)的根本特点”。和李泽厚一样(李氏是本书最经常对话的当代中国思想史家),作者也采取了批判的视角,这在解释“克己复礼为仁”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谓“克己复礼”真的如朱子所说的,是具有回复天理之本然这一本来主义的意义的语言吗?……我仍然认为,“克己复礼”其实是在讨论私我之一己性与社会之共同性之间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礼”理解为与人之共同性、社会性相关联的行为规范的话,那么孔子对颜渊说的话就可以理解成“超越私我一己的立场,重返与人共同的礼,就是所谓的仁了”。对“克己复礼”的这一解读,粗看貌似突兀,仔细一想却也在情理之中。像这样别出心裁的诠释,书中所在多有,比如对“德”的讨论同样值得关注。在理解“为政以德”时,作者提示,最好不要过早把“德”理解为“道德”——因为“德”与“道”是孔子及其弟子早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但后世的人们对那种共识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李泽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德”的原始含义提出疑问,并认为“它的原义显然并非道德,而可能是各氏族的习惯法规”)。在解释“天生德于予”一章时,书中先后列举了伊藤仁斋、诸桥辙次、涩泽荣一等人的解读,作者认为本章中的“德”透露出其初始意涵,即“人本身所具备的、能够影响他方的力量”。在讲“孝”时,作者强调,“为了扩展皇权国家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性的孝道,与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孝’应该没有任何关联”。在讲“知”时,则援引福泽谕吉的观点,告诫读者不要仅仅将“知”理解为获取知识,进而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解读为“什么值得知道,什么不值得知道”——如此一来,孔子与苏格拉底在“知”这个问题上就实现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
我们当然不必赞同书中的所有见解,但正如李泽厚在大力批判程朱理学之余,也不得不承认:“宋明理学确实发掘和发展了儒学宗教性的深度,使人对原典有了另外一层的更深体会。”对于《孔子的学问》一书,我们亦可作如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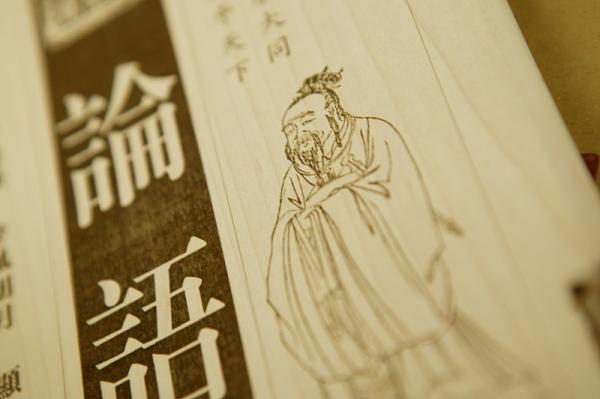
思无邪:现代主义谬误的干扰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一般都把“思无邪”理解为心无杂念,诚直纯正,用朱子的话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在子安先生笔下,伊藤仁斋认为“思无邪”不仅覆盖了《诗经》三百篇,甚至覆盖了夫子之道的全部。而仁斋以“主忠信”为贯穿孔子道德教示之核心,因此“思无邪”也被仁斋解为“直”。作者强调,“这并非一句话的解释问题,而是孔子是怎样理解把握《诗》的,他想怎样向弟子及后代传授这种理解与把握。”可是,作者对“思无邪”究竟应作何解并未给出自己的答案。不过,书中同时引用了荻生徂徕的见解。徂徕认为,诗是多义之物,所谓“思无邪”,“只要随着解诗当时的心境来取义即可”。套用古人常说的话,大约近似“诗无达诂”。作者据此指出,“徂徕的极端偏向多义性的理解,是与以一事(一义)蔽全体的‘朱子们’的取义方式相对抗的。”
有意思的是,李零先生在《丧家狗》中对此章的解释,与徂徕的“偏向多义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新版本。李零引用了《诗·鲁颂·駉》的原文,该诗共有八个“思”字,其中四句句式一样,即“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在这个语境下,不难看出“无邪”与“无疆”“无期”“无斁”语义相近,也就是说,“邪”未必是邪僻的意思。作为古文字学家,李零认为那八个“思”字是“祝辞”,周代占卜用的“思”字有“愿望”的意思。不过李零又表示,“孔子引《诗》,当时引《诗》,多半都是抛开原义,借题发挥,包含许多故意的曲解和误用”,即古人说的“断章取义”。如此这般,读者诸君很可能会发出“思无邪”(思绪万端,莫衷一是)的感叹罢。
说到底,“思无邪”只能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人们的解读总会受到这样那样有形无形的制约。只要开卷,我们即可察觉作者在重读《论语》时的批判态度。林少阳先生在本书导读《近现代日本与<论语>解读》中指出,“假如说子安宣邦的思想史方法论与马克思(1818—1883)有间接的关联的话,那么,这种关联就体现在他的思想史中一贯的意识形态批判上,而这一‘意识形态’,严格上说,指的是遍布的可视及不可视的话语背后的权力性。具体说,子安的思想史方法论,其实直接是受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批判史学,以及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批判社会学的影响。”循此,我们不难理解本书绪言和全书讲解中所透露出的为“学”复权的强烈的心情。“借仁斋的《论语古义》来读《论语》,能够暴露现代学者们的《论语》解读中隐含着现代主义谬误”,而这也成为作者重读《论语》时的一大心结。
直白地说,作者在为“学”复权的时候,似乎在不经意中也犯了现代主义的谬误。作者强调“学”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并认为孔子是第一个提出“学为何物”这一反思性疑问的人;孔子之“学”面对的是已逝的过去,亦即孔子是位“好古之徒”。更进一步,作者申论道,“人就是一种‘学’的存在。人若不首先学父母以及周围的成年人,就无法自立。‘学’这一被动的过程,是人的自立活动的基础。”这些关于“学”的阐释,基本上可以说处于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
问题出在“有教无类”的理解上。作者注意到,“孔子尽管热衷于谈论‘学’,却对‘教’惜字如金。”并强调“有教无类”的“教”并不能与“教育”划等号。在不少地方,作者的这种提示是很有意义且富有成效的——先秦史资料稀少,每个字都值得认真琢磨。不过,物极必反,如何把握“度”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作者批判的对象是现代国家的国民教育,这一现代体制下的“教育”饱含政治色彩,“教育就是由权力阶层对下层民众进行驯化的支配行为”。因此,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完全不具备学习之意欲的学生们,接受早已丧失对学问的意欲的教授们之教育指导”——至此,学校教育的意义丧失殆尽。应该说,作者对现代学校教育的批判有其可取之处,可是把这一批判扩大化,引向批判“有教无类”的相关解读,总让人感觉拳头打在棉花团上,使劲使错了方向。这一批判也导致作者把《论语》中的“教”与“学”对立化,“学”是田园牧歌式的,自由和谐,“孔子学园本身是一个自律的读书人的团体”,而“教”是福柯意味的上对下的规训,“是下层被迫为服务于上层而进行的一种他律性的学习过程”。对“教”与“学”趋于两极的想象,大概就是作者自己也在批判的“现代主义谬误”罢。
另外,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作者在讨论“有教无类”的问题时说吉川幸次郎误读了伊藤仁斋。可我反复阅读书中的两段引文,仁斋的“皆可以化而入于善”和吉川的“都能通过接受教育变成出色的人才”,在精神旨趣上大体是一致的,只不过吉川明确地把孔子定位为“平等主义教育家”,而这相当于“有教无类”的引申义。实在不像作者所指称的那样,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当然,笔者愚钝浅陋,恳请高明不吝赐教。
附带一提,钱穆在撰写《论语新解》时曾参考日本学人的相关著述:“我从日本买回来的三部书,第一部是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第二部是物茂卿的《论语征》,第三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这三部书,正好代表着日本学者治《论语》的三阶段。东瀛学风,本和我大陆息息相通。伊藤仁斋的书,笃守程朱理学家言。物茂卿的书,则相当于我们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龄与戴东原,有意批驳宋儒,力创新义。到安井息轩则受清代乾、嘉以下汉学家影响,实事求是,在训诂考据上用力,而重返到汉唐注疏古学上去。”(《漫谈论语新解》,《孔子与论语》,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物茂卿即是荻生徂徕。钱穆认为仁斋“笃守程朱理学家言”,子安宣邦则直言仁斋是“最早带有自觉意识的批判眼光重读朱子解释的”,两相对照,相差何以道里计!一边读《孔子的学问》,一边思量:钱穆既然读过日本大儒关于《论语》的研究,为何他的《论语新解》最终还是走在朱子的延长线上(这当然也是很大的成绩),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呢?此番重审笔记,大胆揣测钱先生也许只是象征性地“参考”了日本学人的著作,加之他的思想基本上仍在朱熹设置的框架内,越出雷池谈何容易!如果只是以自己的逻辑代入著者的逻辑,那我们不大可能真正领会对方的意旨,到头来,瓶子虽新,而酒仍是旧的。
走笔至此,不禁惕然,硕学泰斗尚且如此,藐予小子在此大放厥词,恐难逃浅薄之讥。好在尚有一点自知之明:本书所涉及的江户古学及日本儒学史(因此也可以成为一种阅读思路),笔者一无所知,但此书在脑力上所造成的激荡效应,就我个人而言,与李泽厚的《论语今解》不相上下。在微信朋友圈读到一句话:思想家的价值,就在于以思想启发思想,而不是以思想压制后人。孟老夫子更是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由此反观《孔子的学问》,庶几近之,而这不可不谓读者之福。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