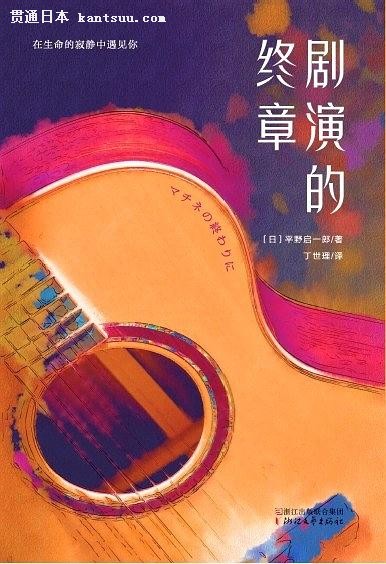|
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今天我们如何创作恋爱小说? 这位年轻的芥川奖得主谈了谈自己如何构思笔下人物的爱情,以及在当代的语境下怎样对恋爱小说进行创新。 潘文捷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1 “我身边的那个人是一生挚爱吗?” 平野启一郎的小说《剧演的终章》曾经在日本民众中引发这样一番讨论。日前,23岁即获芥川奖的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在中信书店举办的《剧演的终章》中文版分享会上,与读者探讨了当代社会语境下的恋爱小说。他称,虽然当今社会,“一生挚爱”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总有某个人在我们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或留下了遗憾,他想要通过作品唤起的正是这份遗憾的心情。 从古至今,无论是《红楼梦》《雪国》这样的经典,还是都市男女的现代言情,读者已经接触了太多爱情故事。但是,平野启一郎的作品依然受到追捧:不仅在日本销售了22万册,获得渡边淳一文学奖,而且将改编为同名电影,由福山雅治、石田百合子等演员主演。他是如何构思笔下人物的爱情,在当代语境下对恋爱小说进行创新的?平野称,他尝试将人物的命运和时代联系起来,并且在作品中展现当代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以及“分人主义”盛行的现实状况。
平野启一郎 人物命运与时代勾连 《剧演的终章》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命运,平野谈到,在小说一开始,女主人公洋子和男主人公莳野就一见钟情,聊得十分投缘。他认为普通人可能难以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这样的瞬间,因此希望“在虚构作品的世界里面,让大家体会一下一见钟情的感觉”。虽然在小说中途,一见钟情的男女主角因为种种原因各自结婚生子,但是他们始终给读者一种彼此心心相印、命中注定的感觉。 在今天,恋爱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多,“一生挚爱”是否已成了一个伪命题?面对这样的疑问,平野称,如今人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伴侣,“一生挚爱”可能会越来越少,可是,即便是和身边的恋人过得非常幸福的时候,总有一些不经意的瞬间会让我们突然想起某段尘封往事。在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人,而且在想起这个人的时候,会觉得“当时如果那样的话,可能现在就不一样了”,心底泛起许许多多的遗憾。 除了“命运般的恋爱”,平野在“命运”这个主题下还想体现出人物的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勾连。他说,在中国作家的作品当中,余华的《活着》让他尤其能够产生共鸣。《活着》的背景是20世纪的战争与战争之后社会体制的变更,个人命运被时代潮流裹挟。在《剧演的终章》当中,平野也把“命运”当作小说的一个关键词,让小说中的人物受到当今世界重大事件的影响。洋子不但是伊拉克战争的战地记者,还介入了后来的中东难民问题,此外她还作为记者揭露了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的核泄漏。不仅如此,洋子的父母也是重大国际事件的参与者:身为导演的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当中与铁托产生了分歧,她的母亲则是遭受核辐射污染的长崎人,连洋子的孩子也出生在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的日子——正因如此,身为经济学家的丈夫没有能够赶上孩子的出生。 作为生活主角的当代女性 虽然在“命运”的主题下进行创作,平野启一郎笔下的女性人物和日本传统文学当中的女性人物的命运已经截然不同。他希望自己描写的,不再是川端康成《雪国》中的那种拥有传统美的女性,而是能够展现出当代社会女性特征的人物角色。确实,和《雪国》当中身世凄凉,只能从事女招待或者艺妓这些职业的女主人公驹子相比,生活在巴黎、以战地记者为职的洋子在外人看来已经是“生活的主角”,“没有莳野也有很好的人生”。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平野看了不少凄美爱情电影,例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电影《第二个月亮》等等,他发现这些作品共通的设定就是男主角要上战场、女主角在家中孤独等待。可是在今天,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已经大大提升,女性也拥有了更多的职业可能性,所以在《剧演的终章》当中,他安排女主角洋子奔赴硝烟弥漫的伊拉克战场,而男主角莳野则在和平的日本与女主角通信,等待她的归来。
周大新 另一方面,平野启一郎在小说主人公的年龄上也放宽了限制。当晚的对谈嘉宾、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指出,即便是在中国的当代作品中,恋爱小说通常描写的几乎都是20多岁青年男女的爱情,年龄最多不超过35岁,可是平野的小说男女主人公都在40岁左右,而且洋子比莳野大两岁。“中国的恋爱小说中很少写这种年龄段人的爱情。”周大新说。平野称,之所以这样写,一方面是今年43岁的他对十几岁的毛头小子那种一腔热血的热恋已经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今天虽然也存在婚姻观念比较传统的人,但是大城市里人们的思想已经更加开明,他们普遍结婚较晚或者干脆不想结婚,只不过由于女性在生育上有年龄限制,所以不少日本女性到40岁前后才会比较着急,感受到寻找结婚伴侣和生孩子的压力。 从“个人主义”到“分人主义” 平野最近在提倡的概念是“分人主义”,他指出,“个人”这个词源于英文单词individual, -dividual是“分开”,而in-的这个词根则为否定,因此,individual意思是不可分开的个人。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文学作品当中,个人常常被当作为不可分离的主体,只有一种性格、一种思想。但是实际上,在如今的生活当中,每个人在和恋人、和家人、和工作场合上的人接触的时候时常呈现出不同的性格。正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可分割的人格,所以平野创造了一个词,叫做“分人”。 平野曾经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分人”的现象是近代社会产生的。在他看来,一方面,欧洲的个人观念源自一神教——一个人完整地对应一位神,人们需要以统一的自己去面对仅有一位的神灵,进入近代之后神消失了,统一的自我也分裂产生出复数的“自己”;另一方面,在日本,人们长期以来都是一辈子做一个职业,但在现代社会职业的要求之下,人们经常通过复数的自己来做不同的事情,这样即使一个做不成,另一个可以做成,还是可以实现自己。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很多年轻人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不断思考到底要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到底要如何去生活。平野给出的答案就是:复数的自己可以在社会的变化中更好地生存。 就小说创作而言,平野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在独处时和在别人相处时都呈现出同样的性格,而托尔斯泰的做法很不一样——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当中,主人公安娜在不同的场景下、与不同的人相处时会呈现出不同甚至迥异的性格,他认为这种做法使得人物的形象更为立体。 在《剧演的终章》当中,女主角洋子也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拥有很多“分人”——作为战地女记者的分人,作为美国经济学者妻子的分人,独自生活在纽约生活的分人,和母亲相处时的分人,以及与男主人公莳野相遇、相恋的分人,彼此不同,各有差别。伊拉克战场上的“分人”带给洋子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与经济学者结婚的“分人”让洋子获得了一段时间的满足。当她思考自己作为哪一个“分人”感到最为幸福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与莳野共处的这个“分人”。“人类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多面性存在的生物,”平野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体现人的丰富性。”
《剧演的终章》 [日] 平野启一郎 著 丁世理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3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本文来自于界面) |
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今天我们如何创作恋爱小说?
作品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相关文章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日本很可能正在重复历史!
早稲田大学“村上春树图书馆”即将正式开放 村上称很紧张
村上春树批菅义伟涉疫情言论:或许只看想看的
日本知名作家宫川东一:我直到30岁才知道,孙中山是我的外祖父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日本或将重复当年的历史
香港邦瀚斯展出多幅草间弥生早期作品
日本又是一年开学季:村上春树向母校新生发表别具一格的致辞
《枫桥夜泊》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
大江健三郎與日本的孟子民本思想
日本文学大奖揭晓:高山羽根子和远野遥获芥川奖、驰星周获直木奖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确定 檎克比朗凭借《swan》获长篇奖
日本文学中的《史记》投影 是莫大的幸运与快事
日本芥川奖和直木奖候选作品公布 驰星周第7次进入候选名单
《They Are Billions》中文版和日本同步发售
日本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
小说版《鬼灭之刃》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前两名
鲁迅怎么就成了日本的国民作家?
日本文豪如何说 I love you
这本书,被许多人视为“日本文学的巅峰之作”
为了宅在家的人们--东野圭吾7本人气小说首次推出电子版
老舍作品在日本
村上春树参加线下粉丝活动 表示“以后可能写长篇小说”
日本平成时代文学的后现代图景
日本的“下流社会”作家
明治时代神秘书店什么样?日本元老级推理小说家为爱书人筑梦